《蛮与痴》:去看看翻滚的浪涛下,涌动着的不竭的力量
2015年浙江省高考理科状元郑恩柏, 进入北大后选择了中文方向,毕业后尝试专职写作,《蛮与痴》是他蛰伏多年后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
本书采用了传统叙事和方言采访交织的叙事形式,其中方言部分极为精彩,借二十余位受访者之口,编织出广阔的社会背景,结合三个少年出海的主线情节,全书既有微观的成长史,也有宏观的群像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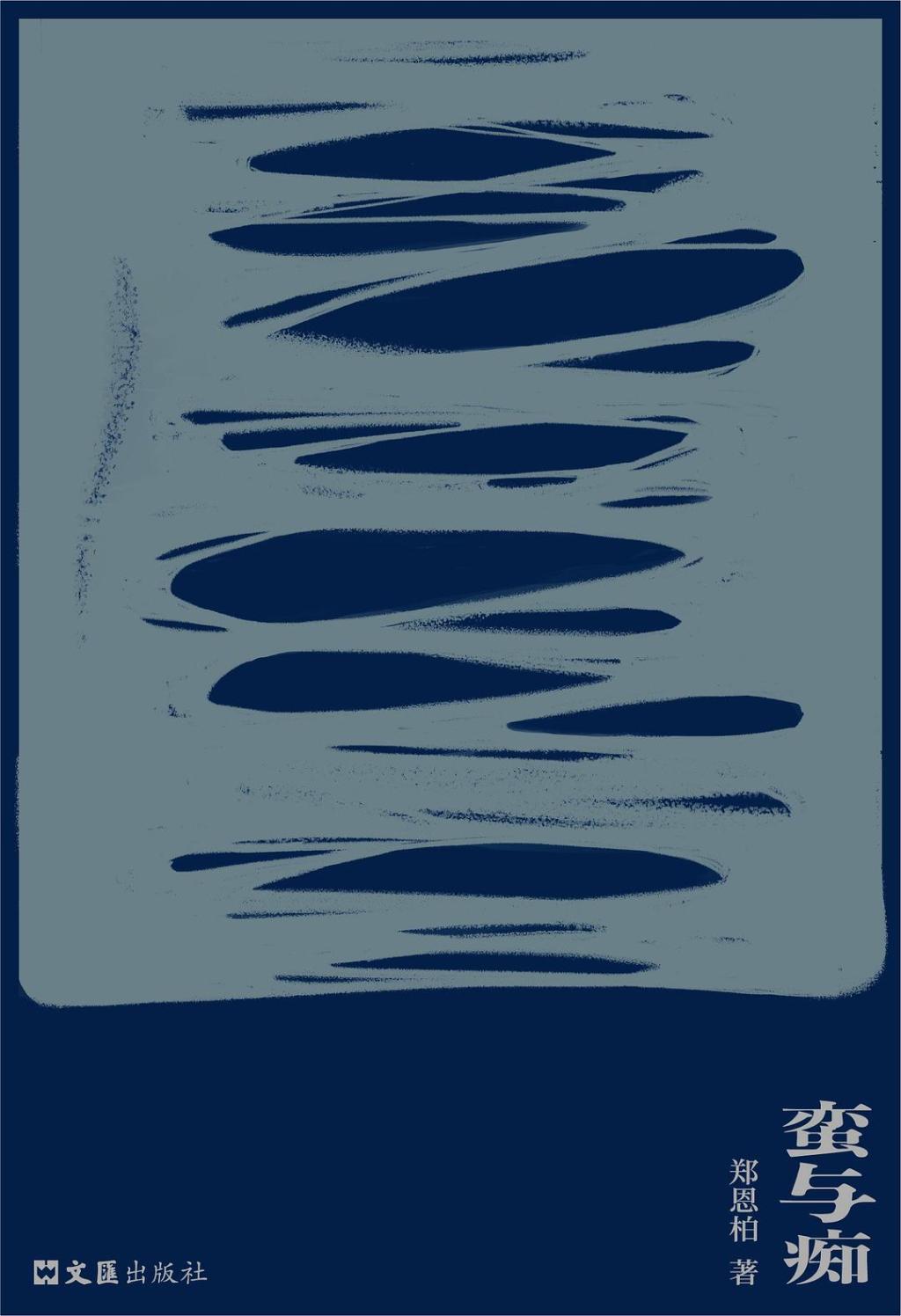
《蛮与痴》书影。作者: 郑恩柏。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打开郑恩柏的长篇小说《蛮与痴》时,正好窗外刮来一阵风,书页顿时在风中不安地翻飞,就像书中藏着一个飞扬的精灵。书页里传出的不是油墨香,而是腥味,那种踏进苍南渔村就能闻到的空气中时浓时淡的特有的海腥味。
第一人称·第三人称·方言和方言改造
要不是十多年前,曾去过温州乐清辖下的蒲岐镇采访东海浪花里讨生活的渔民,对浙闽交界处的渔耕社会有了些许感性认识,还真不太好懂郑恩柏用苍南方言写成的《蛮与痴》。这并不是说笔者能听懂当地的方言,而仅仅是对浙江沿海最南端的渔耕社会有了一份外乡人的粗浅感知而已。
要了解40年前的温州苍南的渔耕社会,还是读读郑恩柏的《蛮与痴》吧,这部长篇小说的篇幅并不长,但小说的时间跨度不小。从浙南渔耕社会在迈进改革开放时代前后的民间故事和世间百态,直到小说中的“我”离开故乡20年后已然成为一名学者,重新踏上归乡之途,试图通过对父老乡亲的访谈,寻找当年一场民间械斗的真相,那已经是三年疫情过后的今天了。
《蛮与痴》的视角独特,首先在于它的叙述方式的独特性,全书虽然分为序曲、作为小说主体的第一至第三部,以及尾声这五部分,但实际上为两大部分构成:用活体印刷的以第一人称呈现的访谈部分,以及用宋体印刷的以第三人称呈现的故事部分。前者不同的人物,除了“离乡之人”以外均采用苍南方言;后者则是带有些许方言口吻的普通话叙事。
在书中,第三人称叙述的故事,是小说的“明线”;而苍南方言讲述的故事,是小说的“暗线”。通常,小说的“明线”会更精彩、冲突更激烈,也更吸引读者;但《蛮与痴》的特点恰恰是采用苍南方言讲述的“暗线”,似乎更本真、更接地气、更原生态,也更加吸引人、打动人。
可以说,这是方言写作、原生态写作的一次成功的典范。仅此一项,就为温州文化作出了值得嘉许的贡献。说实话,笔者甚至不认为我们哪本沪语小说,在这方面比它更精彩多少。按理说,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笔者对沪语的理解程度肯定远远大于对苍南方言的理解程度,但此书的苍南方言就是这么打动人,尽管笔者也曾造访苍南,虽然当时依然听不懂苍南方言,但《蛮与痴》对苍南方言的“还原”和呈现非常成功。
郑恩柏告诉笔者,他为了让更多的非苍南读者读懂难懂程度在中国各大方言里占据“头部”位置的苍南方言,对苍南方言作了四五轮的删繁就简的精心“改造”,删除了过于难懂的表述,而留其精髓。看来,这份“方言的改造”相当成功。有点像风靡欧美的中华料理,常常除了麻婆豆腐还原汁原味以外,其他哪怕红烧肉都多少都已经本地化了而大受欢迎。当然,这不仅是方言改造和方言写作的成功,而是作者对诸多人物塑造的成功。此其一。
明线·暗线·复杂多姿的世间百态
《蛮与痴》中“明线”和“暗线”两者看似各不相干,各说各话,但它们并不是永不相交的“平行线”,而是发生并进行在几乎相同或相近的时空范围内,就如同是从同一块土壤中分别生长出的两支藤蔓,各自生长,又相互缠绕、交错,人物和故事在彼此的生长和延展中得以呈现、呼应乃至交融。“明线”的故事为明勤、明杰、明泽三兄弟“勇闯大海”的青春成长故事,而“暗线”的主角“受访人”则为苍南各色人等,既有油条摊主、修车师傅、“女子械斗队长”、计划生育出逃人、被拐卖女人、改革开放以后“做会钱人”、“离乡之人”(或他就是作者自身)等等,还有“明线”中的重要人物“陈明胜”(名胜阿大)和明勤三兄弟的“阿妈”,也以第一人称登场。如此众多的人物的出场,不仅对“明线”故事的讲述起到了补充完整和时空延展(“东湾生意人”的讲述已经跨越到21世纪20年代初的“新冠疫情”)等作用,更为“明线”故事的展开拓展了一个更为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复杂多姿的渔耕社会的舞台,其意义非同寻常。
再者,作者身为北大毕业生,能俯下身来,认真倾听“最民间”的民声,记录“最接地气”的民情,实属不易,这样的人生态度和创作作风值得大大肯定。毫无疑问,作者非常擅长文学描写,如他写明勤起锚:“锚身沉重,但是尖钩朝上,像即将冲天的炮弹。碎沙随之扬起,又纷纷抖落,如同四散的花火。”一艘小渔船在岸边的起锚,竟然能写成“像即将冲天的炮弹”和“如同四散的花火”,不能不令人折服,因为这些描写展示的正是明勤三兄弟出海时的激情和豪迈。对笔者的这一评说,郑恩柏颇为赞同:“我写《蛮与痴》的时候,确实常常让人物的情绪带着情节走,而不是让人物跟着我设定的情节走。”
作者的文学才气在书中体现得酣畅淋漓,但笔者认为更应当肯定的,是作者对渔民“做海”过程的深入观察和细致描写。在明勤最初上船时手足无措的尴尬中,读者似乎可以看到作者年轻时的身影。也许,正是这份手足无措,让作者去更为细致地观察渔老大们是如何下网、收网、分拣渔获、撑帆、掌舵的。而这一切,既为曾经的苍南渔民、也为温州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真实记录。
故乡·童年·海浪和海浪下的力量
不知道《蛮与痴》是不是可以归为“回乡文学”的一种?作为90后的土生土长的苍南人,郑恩柏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靠理科竞赛和自主招生的方式升学,直到以760分的高分夺得2015年浙江理科高考状元,叩开北大元培学院的大门。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最后选择的方向竟然是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更是不顾家人的反对,选择了文学创作道路。笔者问他是不是在初高中阶段读了哪位名家的哪本小说,才走上了弃理从文的“歧途”?他说,最初的文学启蒙或许是在小学五六年级时一次偶尔走进镇上的一家新华书店,翻开了鲁迅的一本杂文集。因为囊中羞涩,无钱买书,他就站在那里读,深深陶醉其中:“原来一个人可以通过写作来向世界表达喜怒哀乐!”
通常一心从事文学创作的年轻人,整天思绪飞扬,能不翘课已属上佳表现。郑恩柏强调说,他还算守规矩,在北大读中文系时专业课一般不翘,但坐在教室里可能就只是在读自己喜欢的书了。除了鲁迅,他喜欢的中国作家还有王小波、莫言,国外的作家有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智利的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日本的三岛由纪夫和谷崎润一郎等等。
《蛮与痴》是郑恩柏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自认自己更适合写长篇,而不是写中篇和短篇。那“蛮”和“痴”,在这里分别代表了什么?郑恩柏说,“蛮”代表了浙南渔耕社会的原生状态,而“痴”则是指生存于此的众生内心涌动的“执念”,一种不甘于向命运屈服、强烈地渴望改变自身状态的冲动。
作为“访谈者”出现在书中的“我”,相对仍在当地的“原乡人”而言,他是多少已经部分实现了“执念”的“第三者”。如果说,在他年少时离开故乡前,内心充满着迫不及待走向外部世界的青春冲动;而如今他重新归来,童年时代就已熟悉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却前所未有地抚慰着这位归乡游子的心。“童年时在外婆家老屋里度过的时光仿佛又回来了,雨水淅淅沥沥打在瓦片上,星星就在头顶上无声地闪烁,清晨鸡鸣声时远时近……我发现这是我童年时最幸福的时光,而那时候的所有的幸福,都和钱没有关系,都不是用钱买来的。”他说。
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他在《尾声:归乡之路》中写道:
一路下坡,我再次闯进那座弄巷交错的迷宫。两侧房屋像甘蔗节节猛长,仍旧拥挤,仍处在倾毁的边缘。时隔二十年,我已不再执着于低迷的犬吠,却还是不自觉加快脚步,试图逃离记忆的涡旋。踏入沙滩之际,我望向茫茫的前方,日光像万千箭矢射向海面,孩子们褪去衣裤,化作一尾尾纤细的银条,没入水中……
“人只有走近了大海,才会听到海浪翻滚的声音;而如果远远望去,大海只是海平线上波澜不惊的一条线。”郑恩柏说,“我就是想让读者跟着我走近大海,看看翻滚的浪涛下涌动着的不竭的力量。”